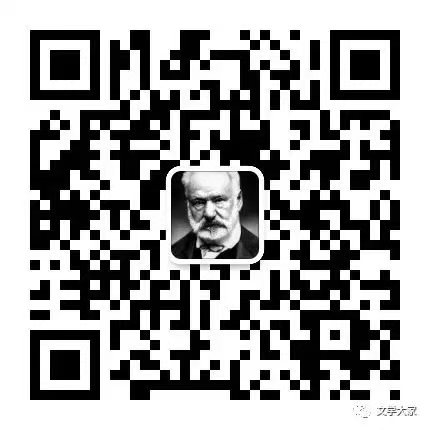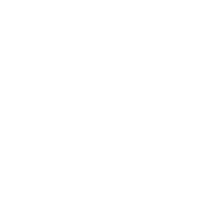
文学大家
media group
放眼未来,着步全球
多方位文化传媒策划
樱桃 ——辞赋里的中国(二)
原创 青桐居士●西岭雪山●丁红宇 来源:文学大家 2019-10-06

樱桃是一年中最早成熟的水果,也是中国人生活中极其重要的水果。樱桃不仅颜色美丽,而且味道鲜美,属于不可多得的色味俱佳的水果之一。因其颜色的特别鲜艳,往往又成为餐桌上一些开胃小菜或西式蛋糕的点缀之物,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增光添彩,并在诸多文学作品中成为扮靓场景的颜色主角。以前樱桃的产量并不多,不用说古代了,即使进入现代,也属于稀罕之物,价格不菲,并不能被多数人享用。进入新时代后,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是价格昂贵的进口樱桃,也已经涌入寻常百姓家。
樱桃最引人注目的,就在于它的颜色,其色如宝石,如珊瑚,如玛瑙,如红豆,光彩熠熠。樱桃颜色之可爱,正如少女红唇之可爱。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或者由于不同的品种,樱桃有着不同的颜色,如同少女之红唇,在不同的光线下面,会泛着不同的梦幻般的色彩。白香山把姬人樊素之口比喻成“樱桃小口”,正是这个缘故。
樱桃之美丽,不只在于樱桃本身果实颜色的变幻多端,更在于樱桃果实的红色与其树叶的绿色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红映照着绿,绿衬托了红,两种颜色都因此显得更加耀眼夺目。这也像极了一个漂亮女孩身上颜色的搭配,其实也不单单在于其樱唇的鲜艳红润和脸颊的艳若桃李,也在于其肌肤的白如凝脂和眼眸云鬓的乌黑亮丽。多种颜色纷呈而不凌乱,便是伟大的自然力量妥帖安排、精巧设计的结果。

因为樱桃的特别美丽,中国历朝历代描绘樱桃的诗词歌赋名句层出不穷,然而一致公认最佳的应该以南宋词人蒋捷之句莫属,其句最为出彩,故而最为出名,给人印象亦最为深刻,且最耐人寻味,堪称“绝妙好词”: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在蒋捷的名句里,“樱桃”与“芭蕉”两种颜色截然不同的植物实现了文字史上前所未有的巧妙组合,寥寥数笔,简简两物,画就了一幅颜色鲜明、灵活生动的中国画,颜色鲜明对比的两种植物组成的映像宛在眼前,却极准确极形象地昭示了樱桃才红,芭蕉又绿,无情的岁月脚步何其匆匆,让人望尘莫及!真是使人感伤莫名。此句只应天上有,人间妙手偶得之。能够写出这种句子的实在是天才人物,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少年时代读及此句,也是不由得拍案叫好,佩服不已。但是那个时候并不太明白其高超艺术手法所在。现在回想起来,蒋捷此句之所以能殝极致妙境,一方面是此句在对植物风貌不吝赞美之同时,也隐含了对于青春美丽易逝不再的无限惋惜之情,以及人生时光匆匆的悲哀无奈,体现了“中国美”与“中国物哀”的无缝对接与融合。“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不正表明美丽的欣赏与时光的流逝并在吗?人生在世,有所爱,有所乐,有所欢,然而同时也必有所恨,有所哀,有所悲。真可谓:樱桃年年红,芭蕉常常绿,而人生之流光一去不复返矣。遥想众人难得相会于此世界一次,纵然欢乐长久,难舍难分,魂牵梦绕,但也终须一别,可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故而苏东坡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岂不令人悲喜交加哉!
蒋捷此句趋于妙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其利用了中国辞赋创作中普遍采用的对仗修辞手法——大部分的辞赋,其实通篇都是对仗句(或者说对偶句)。而作为辞赋句,其第一要求就是工整对仗——蒋捷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形式上就是辞赋句,用其它更为工整的辞赋句“才红樱桃,又绿芭蕉”来代替也是可以的。非但如此,“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除了字面的对仗,颜色上也是对仗,即“红”与“绿”对仗。吾一直认为,对仗是一种类似对称之自然力的伟大力量——伟大的自然遵循对称的原则创造了万物,中国人则不知不觉地向自然学习这种创造法,并在文学创作中将此法运用得炉火纯青。这一将中国文学创作规律与自然科学创造规律结合起来分析的观点似乎他人未曾提出,吾也算得上首开先河了。除了中国辞赋、中国对联、中国律诗,中国建筑、中国古城市规划也大量运用了对称办法。对仗的利用,正是蒋捷此句效果震撼的缘故之一。
正因为樱桃的描写极适合运用对仗句(对偶句),作为描绘世间万事万物的极致文体,中国古代的辞赋作家们写起樱桃来是当仁不让,工笔细腻,浓抹重彩,无所不用其极,营造出了另外一个色彩缤纷、绮丽无比的樱桃世界。

明朝人周履靖的《樱桃赋》(《历代辞赋总汇》第九册七六八零页)中写道:
名叫含桃,又称崖蜜。
在式乾殿前栽下,在华林园内种植。
池流潺潺,映衬着碧绿的叶丛;
朝阳升腾,照耀着红色的果实。
樱桃花的繁荣吸引着蝴蝶翩翩而来,
果实的丰盛吸引着鸟儿在此翔集。
夏天上供给寝庙作为祭品,
与其它祭祀用牲畜一齐陈列;
在月光下赏赐给群臣,
颜色和盘子一样。
经常被黄莺偷窥偷啄,
充当彩凤经常食用的食材。
像蚌珠呈供到宫殿,
像猩红的血液与琼浆和在一起。
像万颗紫色的丹丸悬垂,
又像一片绛色的彩霞装饰。
没有葡萄那样的碧绿晶莹 ,
却有杨梅那样的温暖黄赤。
(名以含桃,呼以崖蜜。
式乾殿前而栽,华林园内而植。
池流而映碧丛,朝阳而照朱实。
花茂兮而蝶来,果繁兮而鸟集。
荐寝庙于夏间兮,共牲齐列;
赐群臣于月下兮,与盘同色。
被黄莺之窥啄,充彩凤之常食。
蠙珠(pín zhū)而供玉堂,猩血而和琼液。
万颗紫丹而垂,一片绛霞而饰。
无葡萄之碧莹,有杨梅之韫赤。)
此赋虽是明人之作,却如同唐人之文,写的是唐朝的事情,想象非常丰富与贴切。此篇辞赋,也将颜色词汇对仗之手法用至极致,将池流(冷色调)与朝阳(暖色调)对应,碧丛(碧绿)与朱实(朱红)对应,花茂(雪白)与果繁(朱红)对应,蝶来(五彩)与鸟集(五彩)对应,黄莺(黄色)与彩凤(五彩)对应,蠙珠(珍珠白)与猩血(猩红)对应,紫丹(紫)与绛霞(绛)对应,葡萄(淡绿)与杨梅(紫红)对应。通过精心谋篇布局,仅用寥寥数物,便营造了一个和谐共处、生机勃勃、色彩缤纷的美好境界。自然的美丽世界已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美丽世界的主角,而中国古典文学通过讴歌自然的美丽世界,则愈加促动人们心生对于现实的美丽世界的向往。显然,最具有能耐的中国辞赋作家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自然颜色的丰富多彩有助于形成别致的中国古典文学之美,他们能够运用中国字典中多种多样的颜色词汇来描绘他们眼中看到的多彩世界,并广泛采用对仗的修辞手法,达到对各种美丽意象进行比较、进而彰显其特征的效果。

清人范驹之《樱桃赋》可谓是诸多《樱桃赋》中描绘樱桃颜色较为细腻的一篇:
当它细白的果实像攒包一样聚集在一起,
垂荫发出深青的颜色。
晨雾浓披,在春寒中稍稍颤抖。
等到樱桃个个像女孩子的耳饰一样悬挂着,
等到樱桃渐渐膨胀欲滴,
泛着光泽如同玉色一样沁透。
既然时间与九熟之稻成熟时同时遇见,
忽然间千万颗樱珠光芒璀璨。
不同的品种间隔分开,
有的蜡黄,有的晶白;
经常供应的美味也是非常美好,
或像少女的脸一样发出阵阵晕红,
或像珊瑚一样一团赤红。
拈着樱桃果实上的小蒂仿佛粘得甚牢,
一个小蒂包含了所有的滋味,
捻着轻轻的红丸而成团成簇,
真是别有一番清美。
晚上放在玉石盘上,
颜色杂乱如同千重红玛瑙,
清早仿佛打开了养殖珊瑚的铁网,
数量如同十斛珊瑚打碎了一样那么多。
(方其细白攒包,深青垂荫。
晓雾浓披,春寒薄噤。
迨个个以珰悬,渐津津而玉沁。
既候交乎九熟,忽光璨乎千珠。
异品间分,蜡黄晶白;
常供亦好,晕赤团朱。
拈小蒂以犹粘,知包全味;
捻轻丸而成簇,别具清腴。
夜设瑛盘,混看千重靺鞨;
晨开铁网,碎量十斛珊瑚。)

樱桃色是中国美的一部分,这就象女人倾国倾城的美色一样,对中国人影响巨大。两者都是自然形成之“色”,都有着无穷的吸引力,来自自然的强大的吸引力。既然是人,生来似乎就无可逃避地热爱这颜色,喜欢这颜色,接受这颜色的影响。这种颜色也不是单纯的一种颜色而已,它还与“光”结合,形成所谓的“色泽”,晶莹剔透,宛如膏泽与玛瑙。人类,包括世间万物,也只有拜自然力所赐,才能形成变化万千、令人浮想联翩的“色泽”。你看看那些健康地生活着的美人,诱人的脸蛋确实如同樱桃一样,脸上的色泽随着角度的变化和阳光的移动,显得愈发鲜活灵动、变幻无穷,又如同不停地展开的一幅幅油画上的肖像,光彩照人,令人目不暇接,神魂颠倒。
要欣赏樱桃的颜色,还不能完全地仅仅依靠樱桃本身,最好是将樱桃的颜色与其它颜色进行相互映衬对比。这也是中国人享受生活和娱乐生活的智慧之一。譬如,在中国人的辞赋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乐于将樱桃与一系列特殊的物件进行组合类比,譬如,樱桃与芭蕉,樱桃与春笋,樱桃与玉盘,樱桃果粒与樱桃叶子的对比,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然而其结果却又是非常的和谐而统一,让人愉悦。
在明人周履靖的《樱桃赋》中,除了叙述樱桃丰富的颜色,还提及了唐朝以来以樱桃为主食的重要活动——樱桃宴。唐朝人之所以发明了樱桃宴,与唐朝人重视樱桃之关系极为密切。唐代之前,樱桃即作为祭祀品进供祖先,加之不易栽培,故而极其珍贵。唐代之后,樱桃种植技术进步,宫里大量栽种樱桃,并建立了专门的樱桃园,又以长安、洛阳两地栽种最为繁盛,后来逐渐从宫殿兴盛到到民间,樱桃方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普遍享用。唐代诗人描绘樱桃之句如雪霏霏,数不胜数。《旧唐书》记载:
景龙四年,夏四月丁亥,上游樱桃园,引中书门下五品以上诸词长官学士等入芳林园尝樱桃,使令马上口摘,置酒为乐。
在唐朝,每年阳春三月,正是樱桃收获之季,朝廷都会用樱桃向祖宗上供,并且赏赐给重臣等人。新科进士放榜之时,新进士们会聚集在一起赴“樱桃宴”大快朵颐。后来,樱桃宴中加入了春笋,又称樱笋厨、樱笋宴。此种文雅的庆祝方式一直延续到清朝还绵绵不绝。樱桃宴或樱笋宴成为了中国文人文化生活中的一场重头戏,许多文人以能够参加樱桃宴或樱笋宴为荣。樱桃宴或樱笋宴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的辞赋作家们初春时节的作品主角。在中国辞赋最大的作品渊薮《历代辞赋总汇》中,《樱桃宴赋》或《樱笋厨赋》佳作迭出,而单独写樱桃之《樱桃赋》者反倒鲜见。

清人吴荣光之《樱笋厨赋》(《历代辞赋总汇》清代卷第十四册壹万叁仟捌佰伍拾页))写出了樱笋宴的环境之别趣,在诸多樱笋厨赋中别具一格,读之令人爱不释手,堪评佳作:
在竹林间盛筵开启,
在花丛下面绮席开张。
让千种珍异食品甘拜下风,
让初夏酒席增添愉欢。
喜欢春笋像玉片一样放在盆里,
看樱桃像霞堆一样待人就餐。
捧出均匀的朱红樱桃,
色彩与葡萄酒辉映交相;
削来新笋,香气在鹦鹉杯上袅袅升腾。
笑入唐朝大美食家韦陟的厨房,
只要有樱桃,
就会感叹何必要有那么多的美味佳酿;
如果桓温夹筷,
樱桃的清味也完全能够担当。
又如同开启龙华之会,
宴席放在兰舸上举行。
在密密的柳树中携带酒壶,
在深深的竹林中长留驻神。
(竹间厨启,花下筵开。
却千重之珍错,娱初夏之尊罍(léi) 。
喜供盆之玉片,看入饤(dìng)以霞堆。
捧出匀朱,色映葡萄之酒;
削来新绿,香浮鹦鹉之杯。
笑登韦陟之厨,庶羞何必;
倘入桓温之箸,清味堪陪。
又或会启龙华,宴移兰舸。
柳密携壶,竹深留坐。)

清人郑炎《樱笋厨赋》(《历代辞赋总汇》清代卷第十四册,壹万叁仟叁佰贰拾贰页)则似乎偏爱以自然野趣的场所作为樱桃的最佳食用环境。在一种自然、闲适、放松的环境里,在一个水绿山青、风清云淡之所,友人之间没有世俗的利益纷争,在大家使用精致的餐具品尝完美味的樱桃后,只有棋盘上对弈的快乐,大家畅所欲言,无所顾忌,耳边传来的只是鸟语琴声:
以银匙轻挑,用檀木制作的筷子刺取。
味道不淡不浓,没有膻气,
也不会让人感觉吃饱。
礼轻而言欢,朋友因之而安逸。
世上的忧虑难以干扰,
人间的灰尘烟雾都被过滤。
有时在储食橱边小酌,
有时在尚书省大快朵颐。
吃得津津有味而聚精会神,
因此不会感觉簟子过于清凉,
不会感觉语言繁絮唠叨。
遥远的山脉如同画一样,
长年的积水常有新水注入而常流常新。
云峰恬静而不繁杂琐碎,
鸟语喉咙滋润而皆驯服。
琴声和谐而物产丰盛,
酒味浓厚而心情醇美。
可以依栏而对弈下棋,
可以坐在石头抡起钓丝。
既可以与贤惠的主人一起心情畅快,
也可以与嘉宾相互欣赏愉悦。
(挑以银匙,刺之檀箸。
不淡不浓,非膻非饫。
折简言欢,盍簪由豫。
世虑难撄,尘氛都滤。
或小酌于纱橱,或大烹于粉署。
簟岂碍于清凉,语无劳于繁絮。
遥山如画,积水常新。
云峰恬而不碎,鸟语润而皆驯。
琴风调而物阜,酒味厚而心醇。
可依栏而对奕,可坐石而重纶。
既畅怀于贤主,亦属意于嘉宾。)

清人华文模的《樱笋厨赋》(《历代辞赋总汇》清代卷第二十三册,贰万贰仟陆佰贰拾贰页)也写出了采摘樱桃与春笋的别样乐趣:
清晨去摘朱樱,
果实挂得枝条下垂,
如同星星点点。
晴天去挑绿笋,
山径弯弯曲曲被薄雾轻笼。
春末三月,春莺吃不完的果实,
像红色的宝珠一样光亮鲜明,
一夜之间,春笋的样子,
像碧玉般精致玲珑。
(晓摘朱樱,低枝星落;
晴挑绿笋,曲径烟笼。
三春莺口衔余,红珠的皪(de lì);
一夜猫头茁后,碧玉玲珑。)

清人吴赞的《樱笋厨赋》(《历代辞赋总汇》清代卷第二十三册,贰万叁仟陆佰贰拾贰页)写道:
盛宴开始在初夏,
美味胜过春天的芳菲。
樱桃红如烈火,春笋白过冬霜。
陈列美食而杯盘增色,
品尝时新而齿颊留香。
(厨开夏始,味胜春芳。
樱红似火,笋白于霜。
馔而杯盘增艳,尝新而齿颊留香。)
又道:
想象那樱桃树倚靠着苍穹,
舒展开她花朵的雪白。
结起了果实饱含丹色,
绽放光辉而发出耀眼通红。
开始则在枝头挂缀,
一颗颗像红豆啊几只几只地一起垂下来。
然后就在树叶底下均匀地排列,
果实像染上了朱砂啊成百上千。
任凭泼上去春雨,
仍然像红宝石一样团簇千堆。
如果只是楝子之风轻轻吹打,
她依然像七尺珊瑚一样完整无缺。
(想其树倚霄青,花舒雪白。
旋结实而含丹,乍生辉而耀赤。
始则枝头初缀,颗垂红豆兮几只;
继则叶底匀排,料染朱砂兮累百。
任泼上桃花之雨,仍然火齐千堆;
仅敲来楝子之风,未碎珊瑚七尺。)

从樱桃宴的开设,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和娱乐智慧,那就是善于做樱桃文章,这篇可以打满分的樱桃文章不只是记述种樱桃、摘樱桃、吃樱桃、赏樱桃的过程,也不是以樱桃为题材的诗赋,而是将一席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樱桃宴或樱笋宴做出仪式感,做出文化,做出习俗,也让参与者吃出了荣耀与历史,吃出了欢乐与热闹,吃出了记忆与向往,颇有点石成金的味道。倘非中国人办事聪明、善动脑筋,则如何解释为何独独中国古人会有这种独特的樱桃筵席仪式呢?为何中国古人独有这种樱桃盛会的乐趣,而西洋人或美洲人就没有呢?我想来想去,在《西游记》中的天上,倒有一个蟠桃会,与人间的樱桃宴颇有些类似。蟠桃会在西王母诞辰三月三日举行,与樱桃宴时节完全一致。在蟠桃盛会中,蟠桃成为筵席的食物主角,也只有象“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帝、十洲三岛仙翁、各宫各殿大小尊神”等重要人物才能被西王母邀请“俱一齐赴蟠桃嘉会”享用蟠桃,这与樱桃宴中只有皇帝近侍、朝廷重臣、新科进士才能受到皇帝的恩赐之情形是何其的相似。我想那天上的世界,于欢乐丝竹声之中,天神毕集,仙女如云,觥筹交错,美酒夜光,器具是何等的精致,食物是何等的丰盛,乐曲是何等的悠扬,环境是何等的风雅,场面是何等的庄严,气氛是何等的欢乐,怎不令凡间的我们心生向往!总之,两种宴席均非常人所能及,入席其中对于受邀参加者都是一种无上荣耀与尊贵身份的象征。然而可惜的是,现实生活中虽然有硕大的仙桃,但却没有蟠桃,也不曾有过蟠桃盛会,只有樱桃宴稍留余韵,到如今也已经烟消云散了。我想,吴承恩对于蟠桃盛会的想象是否就来自于樱桃宴呢?这还是有非常大的可能的。《西游记》这部小说十分特别,绝对不能简单地将它作为一部神话小说看待,它其实是现实的翻版,生活的譬喻,若与现实生活对照阅读,肯定会更有意思。

然而,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无论是樱桃宴、樱笋宴,还是蟠桃会,都说明了古代中国人乐于且善于将一件本身无中生有、无足轻重、可大可小的事件办得更隆重一些,更欢乐一些,更盛大一些,体现出一种认真的生活态度、雅致的生活情调、崇高的生活品位,同时也反映出我们中国的古人热爱生活,也非常善于发现生活中的乐趣,最后将之逐渐上升到仪式和风俗的高度,让中国人一代代传承下去,并在悠久的文化继承中增添生活的乐趣。中国古人在中秋节时赏月亮吃月饼,是那么地慎重其事,摆香案,叠月饼,行祭礼,念颂文,一家人和和融融地团聚在月光下,对着一轮皓月展开一系列错综复杂、富有文化底蕴的拜祭活动,然后一齐品尝美味佳肴。这些都与樱桃宴或樱笋宴颇有些相似。现在这种形式又开始逐渐恢复与盛行开来,这是一种传统的继承,文化的复兴,也是时代的进步。现代人逢年过节,往往除了吃,还是吃,吃也不讲究个仪式和文化,大多数时候只会狼吞虎咽,如猪八戒吃人生果——囫囵吞枣不知味,令人笑掉大牙。现代的某些中国人真要多学一学中国古人的智慧,食东西也要食得文雅一些,要像个高级动物,而不能像低级动物,把食物往嘴中胡乱一塞了之、一灌了之、一吞了之。最可惜可恨的是,现在总有那么一些中国人,既不乐于也不屑于继承有趣味有快乐有内涵的传统文化生活形式(尤其是传统文化节庆活动),也更谈不上善于发掘新的娱乐生活项目,形成新的快乐生活主题,让中国人的生活更加美好。为什么随意时代的进步,这种生活的乐趣反而退步了呢?甚至没有了传统娱乐事件的踪影?总之,他们似乎要将中国古人遗留下来的各种趣味生活形式彻底打破,方才善罢甘休,他们似乎要将现代中国人生活中的每个生活细节都弄得乱七八糟、面目可憎、了无趣味,他们才能开心,才能遂了心愿。这真是可恶之极,还不明白他们是不是中国人。对于这些中国趣味生活的破坏者,应该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将他们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或者应该像鄙视痛恨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只有将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逆子、伪卫道士们一网打尽,钉上中国文化的耻辱柱,未来的中国肯定才会有更多更丰富的生活情调与趣味。总之,世界本身已经是如此的无趣,再加上这些内心丑陋、面目可憎、行为粗鄙的人而变得更加的无趣,此时的我们便没有办法,只能千方百计避免这些丑陋的人的影响,自己偏要在无趣的世界中找些乐趣出来,即使是最简单的一日三餐,我们也要努力地吃出趣味,吃出品位,吃出快乐,吃出情调,吃出精致,吃出文化。明白了这个道理,在未来的诸多中国节日里,相信中国人会较西方人更为快乐,这也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现如今,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了樱桃宴,樱笋宴,也当然没有蟠桃宴,也没有了中国文人的雅集,没有了曲水流觞,没有了猜灯迷、行酒令,像消失殆尽的中国特色老物件一样,许多许多有趣味的中国特色老事件也都一去不复返了,有些失去得莫名其妙。然而,以一些特色水果为聚会由头的宴会近几年在民间倒是逐渐流行开来,真是幸运得很。譬如,樱桃采摘游,春笋采摘游,蓝莓采摘游,杨梅采摘游,桃子采摘游,桑椹采摘游,等等,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了,在采摘活动结束后,大家往往一同品尝水果,交杯换盏,聚餐饕餮。这些民间的水果采摘活动可能不如樱桃宴、樱笋宴那么隆重而庄严,也没有形成樱桃、樱笋那样的餐饮主题,但是,其毕竟以水果为活动主题,而且内涵更加丰富,融合了旅游、踏青、观赏、采摘、品尝、聚会、分享、赠别等诸种乐趣,活动形式丰富多彩,也算得上是中国人娱乐生活意识和精致生活意识的觉醒吧!
在历代诸多辞赋中,除了基本上都会写到樱桃宴、樱笋宴盛况,文学家们常常还会将此两种高规格的宴席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典故加以利用,或作为一个重要的题材加以发挥,也有人将老百姓普通生活中的樱桃事件作为题材予以发掘描述。例如,清朝范驹在其《樱桃赋》(《历代辞赋总汇》第十三册壹万壹仟捌佰柒拾陆页)中提及:
杜少陵作客花潭,野人亲饷;
王摩诘拜恩蓉阙,中使分携。
“王摩诘拜恩蓉阙,中使分携”指的是唐朝大诗人王维在皇宫门前两旁的胭楼(“双阙似芙蓉”)中接受皇帝赐赠樱桃的盛况,事出王维之名篇《敕赐百官樱桃》。而“杜少陵作客花潭,野人亲饷”之情形则来自唐朝大诗人杜甫的名篇《野人送朱樱》:
西蜀的樱桃原来也是如此自然鲜红啊,
好客的乡野之人赠送给了我满满的一竹笼。
果实已经熟透了啊,
几番细致的摆放却还是不小心将它们弄破,
令人惊讶的是上万颗樱桃竟然都一样的滚圆匀称而相同。
回想当年在门下省任职时,
我曾经蒙受皇帝恩赐的樱桃,
退朝时双手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出大明宫。
唉!金盘玉箸早已成往事回忆,
今日尝新之时,我已漂泊天涯任随身体如同转蓬。
(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
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
忆昨赐沾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
金盘玉箸无消息,此日尝新任转蓬。)

杜甫是我最崇拜的中国大诗人之一,此诗十分令我喜爱。面对万颗樱桃的统一形状,伟大的诗人发出了仿佛来自孩童的天真浪漫的疑问:“为什么上万颗樱桃竟然如此圆得匀称而相同?”是啊,上万颗的樱桃,每一颗的樱桃大小相差无几,而且颜色又高度的一致,它们为何能够不约而同地地生长?它们为何能够达到如此高度统一的形状?它们如何做到在统一的时间一起成熟奉献给人类?樱桃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几十亿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性别,而几十亿个人的大小、结构、形状、表情、行为都极其的相似。你看世间的美人,更有着相似的构造,光滑的皮肤,明眸与皓齿,发髻如云,曲线玲珑。而对美女们美丑与否的评判,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民族却都有着异常相似的标准。虽然具体的人表面看起来迥然不同,但是迥然不同的背后却又是高度的结构与本质的相似性。这可真有意思。“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隐含在这种相似性的背后的力量——天然力,或者说是自然力,是多么的强大而无可抗拒。想起来,美人和樱桃是多么的相似啊。
《野人送朱樱赋》(《历代辞赋总汇》清代卷第十九册,壹万捌仟柒佰玖拾壹页)一文中,清人陶然用富有想象力、特殊的辞赋语言也描绘了一幅野人送朱樱图:
老农家扛着一筐樱桃,来到我的草堂。
樱桃吸引了鸟禽在树底上偷窥,狗吠叫在篱笆旁。
分享了邻居家的甘甜,安慰了旅客的凄凉。
乡野之人一笑了之,劝诗人不要客气推辞;
大诗人几回细数樱桃,呼唤着小儿子一起来共同品尝。
(野老承筐,携来草堂。
禽窥树底,犬吠篱旁。
分邻家之甘甜,慰旅客之凄凉。
一笑陈词,谓先生其勿却;
几回细数,呼稚子以同尝。)
好一幅野人送朱樱图!在杜甫的心中,野人送朱樱,如同帝皇赐朱樱一样,令其深刻铭记。由于野人送朱樱的情节感人至深,也极为符合中国文人向往的闲云野鹤、隐姓埋名的生活追求,中国古代的辞赋作家往往喜欢用这段场景作为赋题,并产生许多的辞赋杰作。野人送朱樱亦从此成为了中国人心目中万世不朽的一幅图画。美丽的樱桃与农村风光,乡野之人的纯洁与盛情,这些都成为了历代诗人不断讴歌的主题。而在我的记忆中,也有这样的一幅以樱桃为主题的画面,也正是由于主角樱桃的闪亮登场,而成为我往昔世界中的永恒记忆。令人诧异的是,这幅图画偶然舒展在我六、七岁的孩童时光,如今依然在我心中长存。
从一条小弄堂不慌不忙地踱步出来,仅走二百米至三百米,就从我家走到了千年古镇义乌佛堂的老街上。向左拐没有几米,便是佛堂供销社的水果小卖部,高不及我腰的柜台平面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个木框,木框里琳琅满目地摆放着各种应季水果,而今留在我记忆中的就只有美丽的樱桃了。百货商店的服务员当时颇为规矩,个个身着雪白的围裙,戴着雪白的帽子,她们笑咪咪地站在柜台后殷勤地招呼着来来往往的客人,服务态度相当地好。灿烂的阳光越过屋檐,一簇簇或赤黄相间或胭脂红的樱桃泛着晶莹的光芒,像极了玛瑙,像极了珍珠,晶莹剔透,异彩纷呈,层层叠叠,安安静静地堆放在木框里,待人购买品尝。少不更事的我居然也被樱桃这种自然的光泽、靓丽所吸引,竟然久久地站立在樱桃前面,欣赏着樱桃,久久不愿离开。当然,其中肯定也有嘴馋的缘故——但在我的印象中,却没有到佛堂供销社的百货商店购买水果品尝的经历。

令我至今仍然感到惊奇的是,义乌佛堂人对于樱桃的称谓居然是“樱珠”,读音为aijü,就叫这种像珍珠一般大小的小颗樱桃而言的,因为过去并没有看到过硕大的车厘子。而据宋朝陆佃之《埤雅·释木》:
(樱桃)其颗大者或如弹丸,小者如珠玑,南人语其小者谓之樱珠。
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果二·樱桃》(集解)引苏颂曰:
樱桃处处有之……小而红者,谓之樱珠。
义乌佛堂人对于小颗樱桃的方言称谓竟然与千年前的古人对小颗樱桃的称法一模一样,这是何等的有意思!又是何等的文雅啊!义乌一方言学家说过,义乌方言里有着颇多的有音、有义而不知定什么字的方言,其实这些字,有许多是古韵书、古今字典里早就有的。果不其然。
中国的樱桃辞赋引发了我如此多的遐想,这是樱桃的功劳呢?还是中国辞赋的魅力?我想,樱桃美丽,爱美之心亦人皆有之,然而,对于樱桃美的欣赏、品鉴、感悟与理解,还是需要借助中国辞赋作家们的描绘之才。世界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中国古典辞赋作家们就是有这么一双慧眼,就是有这么一枝五彩神笔,能够将尤物之美发挥殆尽,描绘细腻,比喻精工,浓抹重彩,在“美”这一万篇必有、万世不改的永恒文学主题的指引下,无论是细节的观察,意象的组合,还是修辞的运用,词汇的驱遣,都是无所不用其极,让我们愈发无可救药地爱上美丽的中国大地上美丽的自然万物。
到中国辞赋的世界里,去找寻正宗纯粹的中国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