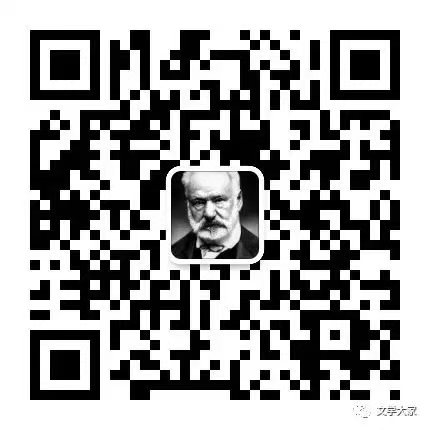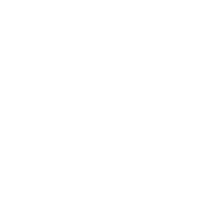
文学大家
media group
放眼未来,着步全球
多方位文化传媒策划
桃花 ——辞赋里的中国(一)
原创 青桐居士●西岭雪山●丁红宇 首发于文学大家微信公众号 2019-09-05
或成蹊而无言,或偕李而重行。
或向日而分行笑,或迎风而共一香。
这几句清人陆求可《桃花赋》里的佳句,写得桃花活灵活现,又颇有生机与趣味,同时也写出了桃花缘溪行而构成的美景画卷。
这里先解释一下,我之所以把赋句如同诗句一样分行排列,也有我的思考,就是,赋是文与诗的融合体,属于一种跨界文体,她是文,更是诗,是一种史诗体裁,是中国人难得的长篇大论。而诗是颇讲排列的,特殊的排列就能够表达出诗的意境与美。正因为此,所以,我一贯是主张把赋句当成诗句来排列的。这种排列,可以彰显赋句极其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展现赋句之美,达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这是中国美学与文学都极力强调的)。这也像极了观赏桃花一样,我们并不希望单调地平视桃花,而希望从各个角度以仰视、俯视、侧视、探视等多重的角度去观赏桃花,并且能够把桃花的各种姿态都欣赏个遍。人也是如此。
清人陆求可《桃花赋》只是中国辞赋大海里的一个珠蚌。最近,由于回忆我的故乡古镇佛堂之桃林的愁绪,我重点阅读了《历代辞赋总汇》中的所有桃花赋,由此产生了许多的感慨,不吐不快。阅读各式各样的桃花赋,不但感觉古人笔下之桃花,实在是非常的艳美,更由于辞赋是一种极致文学,因此,觉得在古代辞赋作者的笔下,桃花显得更加别致的艳丽与窈窕,而且有着许多别致的趣味和情调。这些别致的艳丽和窈窕,还有别致的趣味和情调,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只是被极少数人所研究和欣赏。殊为可惜与遗憾之事。
灼灼倚兰而放,夭夭映水而芳。
娇姿敷而锦锈缀,红艳簇而胭脂妆。
妖艳溪畔而吐,烂漫园中而扬。
似吴姬丹唇之媚,如越女红脸之昂。
这是明人周履靖的《桃花赋》中的佳句,我查了网络,好象并没有,可见还未得到广泛的传播,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前所未闻。虽然从中国字美丽的外形即可感受其所绘意境之美艳,但是似乎也很有必要必须翻译一下。这几句赋句的意思是:
桃花依靠着兰花儿开放,
窈窕的姿态映照着水和芳香。
娇小婀娜的姿态铺敷开来,像锦绣绸缎一样点缀着。
红艳艳的花朵簇拥着,像极了美人脸部化了美妆。
她妖娆的身姿在溪流旁边绽放,
她浪漫的身影在花园中飞扬。
像吴国的美姬红唇一样妩媚,
又像越国的女孩抬起了她绯红的脸庞。
中国的极致文学体裁——赋将桃花写得这么美,更勾起了我对故乡的无限回忆与向往。因为在我记忆中的故乡,原本也有这么美丽的一大片的桃林,占据了我的极少数的记忆宝藏珍品格的位置。在我年少时记忆中的故乡——古镇佛堂,有一个村庄叫下市村,是我奶奶的祖居地,离我的老家仅有近千米之遥,就有这么一种伟大的美,令人窒息的美。对于这种美的欣赏与喜欢,仿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性情,是一种浸骨入髓的固疾顽症。即使是年幼的我也能够感受到这种美,领悟这种美,并为她所迷惑,对她情有独钟。
我记忆中的的桃花世界是这样的:当时我大概只有五、六岁的光景。我记得我跟着父母到田野里干农活,他们在田地里劳作,就让我在桃林中兀自玩耍。在田地里辛勤的他们随时可以看到我的一举一动。在我休息与玩耍的时间,我感觉那一片桃林是一处人间天堂。我当时玩累了,躺在土坡上,那土坡上的青草被焚烧过,显得更加干爽,因此躺在上面就如同躺在一块厚厚的毛毡垫上。我其时是躺在一株足足有数米高的桃树下,我向天空望去,艳丽的桃花的花朵一丛丛地,舒展在蔚蓝蔚蓝的天空之中,粉红色的桃花与天空的蔚蓝形成鲜明的对照,桃树如同珊瑚树一般亮丽璀璨。现在回忆过往,当时的情景就如同一幅幅画卷,而当时年幼的自己就是画中人,是标准中国画中的中国少年。
离桃林不远处,就是一条蜿蜒曲折、清澈见底的小溪,伸展到空中的桃花映照在小溪中,小溪的蜿蜒形成了桃林的曲折多姿。这条小溪的水是通过水泵站从义乌江上抽送上来,流经了我家乡竹园村许多户人家的屋前。想起来,这确实是一副类似于桃花源记中的风景。这处影像就是人世间妇孺皆知的桃花绝胜美景,就是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中的桃花了: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对于这种历经千年而不衰的中国美的灵敏感觉,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独有。在中国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人心中,在许多伟大的辞赋作家心中,完全有着相似性的感受,可谓“古今同感”。
清代慈溪人叶士俞在其《桃花赋》的开头所写的一首五绝诗,仿佛就是对我的家乡景色工笔画一样的描绘。由此可见,对于桃花的种植与布置,或者说对于桃花的鉴赏,中国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个性独特的方法与哲学:
莺声流碧溪,蝶梦锁红烟。
桃花初裹露,霞碎锦云天。
夕阳西下,远处村庄中的炊烟袅袅升起。我在桃林中,看到父母与同村的乡亲们劳作结束,沿着潺潺溪滩,一路荷锄归来,他们的身影在明丽的桃花中若隐若现,在空灵中,隐约仿佛听到了他们爽朗的笑声,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与幸福之感受。我离开桃林,呼喊着,向父母奔去。这又形成了一幅“荷锄桃林边”的美景。
佛堂下市的这一片桃林,应该算得上佛堂数百年来的一景。对我理解《历代辞赋总汇》中清人的描绘极有帮助。
清人俞显在他的《桃花赋》(《历代辞赋总汇》清代册第10册9188页)是如此描绘他眼中的桃花的:
其或路转清溪,源通白石。
本住秦人,曾来晋客。
树短当檐,枝斜拂席。
忽迎渔父之船,每绕耕夫之宅。
故以烨烨丹葩,娟娟碧条。
围锦障之重重,缀金铃之小小。
清人俞显在他的桃花赋写出了桃花与其它物的和谐之美。他的赋表达出了中国人对于这种和谐之美的追求。显然,在清人俞显的眼中,桃花最适宜临溪而树,桃花与流水形成一幅中国画的最佳构图,在流水的源头随意地安放几块嶙峋白石,粉红的桃花三三两两沿溪一路漂流而下,这是一幅何等 美丽的画卷!此外,桃花的种植地点也应该极为讲究,应该就是在渡头或码头边,与碧水褐陵或者与白墙黑瓦相映衬。正因为有了自然与人类的精心妥帖布局,中国人就有了桃花“忽迎渔父之船,每绕耕夫之宅”之趣味。
说了这么多,无非想证明故乡的桃花林是如何有力地在一个尚未始龀的小孩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的。深刻的印象总是有着充足的理由。这充足的理由之一,就是自然美,理由之二,还有与人工物相协调相和谐的和谐美,这种和谐之美是中国美的一部分,对于这种和谐美丽的欣赏又是中国鉴赏学中历久弥新的一部分。
应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桃花源记”的缘故罢,中国人对于桃花与溪流的组合的爱好深入骨髓。甚至有专门的“桃溪寺”命名。这是一所位于贵州省遵义西南郊的中国佛教名寺院。桃溪,极简致的两个字,就将一幅桃花与溪水绝妙搭配的景物画呈现在读者眼前。中国人极喜欢桃溪,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物不可抗拒的与生俱来的美,另一方面,应该与受到《桃花源记》和李白的《赠王伦》感染有关。在这些辉煌的著作中,传统古典的中国美在里面静静地“潜伏”着。
桃花虽然如此之美,而且在中国人的文化体系中,桃花的意像分量不可谓不重。中国70余万首古诗中仅直接描写桃花的诗就有8000多首,占比重不可谓不大,但是,中国人对她的开发与利用还是有所欠缺,无论是她的品种开发,还是她的经济价值,都还没有做到极致。这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这个事情确实显得奇怪。桃花的故事,有点类似银杏的故事。郭沫若在《银杏》中叹道:
可是我真有点奇怪了,奇怪的是中国人似乎大家都忘记了你,而且忘记得很久远,似乎是从古以来。我在中国的经典中找不出你的名字,我没有读过中国的诗人咏赞过你的诗。我没有看见过中国的画家描写过你的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你是随中国文化以俱来的恒古的证人,你不也是以为奇怪吗?银杏,中国人是忘记了你呀,大家虽然都在吃你的白果,都喜欢吃你的白果,但的确是忘记了你呀。世间上也仅有不辩菽麦的人,但把你忘记得这样普遍,这样久远的例子,从来也不曾有过。
虽然中国人没有像忘记银杏一样忘记桃花,但是桃花却往往停留在诗句中,停留在漂亮的文章里,也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保护与利用。这点与日本人对于樱花的开发比较起来,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段不小的差距。
我以为,桃花是一种极美丽的植物,她不应该只被种植在田野里或山坡上,应该把她当作一种重要的景观植物广泛地种植或点缀在各个地方,譬如,学校、公园、绿廊、行道、小区,等等。并且善于利用桃花营造古人曾经表述过的种种景观。当代中国人几乎可以不用再动脑子,只要往古人的书籍中寻找到桃花名篇,自然可以找到最妥帖的布局桃花景观的妙法。不只是桃花如此,几乎所有的各种景观植物的布置,以及园林、山水、房屋、树木、寺院的架构,在中国人的文学世界中都有着大量的丰富多彩的实践。这是中国人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幸运之一。
非但如此,桃花在中国人的感情生活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不是纯粹的植物那么简单。桃花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在中国人的文学世界中,与美人、爱情以及对美人的品鉴欣赏、对爱情的胶着执意密不可分。作为爱情的信物和寄托爱慕之情的载体,桃花起到了颇为特殊的作用。轻视桃花甚至弃绝桃花,是一种类似于犯罪的行为,应予以谴责和鞭挞。
众所周知,在动物学中,蜜蜂是传播花粉的使者,这种传播让植物得以繁育延绵。如果没有蜜蜂,人类的灭绝指日可待。固然,把桃花的作用拔高到类似蜜蜂对于人类命运的重要性显然夸张,但是,两者之间确实还是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从中国古人的辞赋作品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桃花对于形成中国人特殊感情和特殊审美经验的作用。
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桃花与美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对于美人的形容有着较多的桃花专用语,诸如粉面桃腮,桃花面,桃色,桃花脸,桃花妆,等等 。所以,在清代杨恩本的《桃花赋》((《历代辞赋总汇》清代册第11册10582页)中,如此写桃花:
远含绯而送情,近渥丹崦掩 。
至如檀脸将舒,粉腮微破。
纷缦似醉,葳蕤半销。
越女笑而含颦,齐姬醒而犹卧。
若乃嫩绿翦新,娇红出态。
写两靥之胭脂,发双娥之石黛。
......
至如若木停驭,
若夫映日正酣,暮云瞥翘。
清代慈溪人叶士俞在其《桃花赋》中这样写到:
丽女揎东风之袖,妖姬凝北苑之妆。
见新英之灿烂,觉春思其飞扬。
绕蜂声于簾幕,落乌语于纱窗。
喜娇红之销恨,折一枝以赠郎。
若夫金闺迟暮,玉貌黯伤。
风敲筝玉,花影动墙。
红云满树,人立斜阳。
廋春风之人面,悲落英于池塘。
更数枝之映水,浴红影于鸳鸯。
把桃花与人的关系写得如此美轮美奂,美得甚至令人有窒息之感。首句将桃花比喻成“丽女”和“妖姬”,令人通过想象美女的粉黛之色而思桃花之美艳非凡。第三第四句“见新英之灿烂,觉春思其飞扬”直接挑明了桃花对于撩动春思的作用。“绕蜂声于簾幕,落乌语于纱窗”则如同两幅浓抹重彩、细腻工整的中国工笔画,描绘了在簾幕和纱窗这两个桃花摇曳之处的蜂绕乌语之景。说是说桃花招蜂惹蝶的作用,但是,这两处却是美人时常驻足春思、眺望平视之处,令人不由得不遐想美人玉貌与桃花花瓣交相辉映的情景,以及美人对花思人的惆怅思春情形。如此写来,桃花之艳丽大增,美人之艳丽尤甚。“喜娇红之销恨,折一枝以赠郎”就恰到好处地点明了用花作为定情之物,以慰相思之情。这跟“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何其相似。此处极其鲜明地证明了中国人欢喜用桃花作为爱情的信物。
“若夫”以下几句,以桃花的艳丽反衬爱慕之心受挫之后的黯然感伤之情,用明亮之色来对比增加阴郁之情。尤其残酷的是,这个思春美人在目睹桃花落英之时,却偏偏还要面对池中嬉游的一对鸳鸯,可想而知,这对寂寞的美人也是一种折磨。
在清代慈溪人叶士俞《桃花赋》中,接下来几句尤有特色:
落飞燕之红泥,采仙蜂之红蜜。
印游女之鸠头,扑佳人之蝉翼。
留风灼灼,映日夭夭。
名姬公子,杂还春郊。
幕花而羽觞满酌,席花而纨扇轻摇。
散酒香与花气,更金粉其光撩。
唱竹枝而归去,留夕照于花梢。
以上几句,甚有中国趣味与情调,富涵中国人审美之特性。“印游女之鸠头,扑佳人之蝉翼”两句,极细致精致地写出了桃花花瓣轻飘飘地无意落到游女之鸠头与佳人之蝉翼的美好瞬间,令数百年后的我们依然感受到作者的用心何其良苦,他用极细腻的为人不及的文笔将美好瞬间捕捉定格。“幕花而羽觞满酌,席花而纨扇轻摇”两句则将古人室内缘由桃花所营造的浪漫氛围推向极致,在一片片飘洒着朵朵桃花如同满天星辰的空间里,在一片片桃花落英敷满地面的室内,美人轻摇纨扇,在纨扇轻摇间,读者们仿佛真切地闻到了桃花之香气袅袅。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地方大规模地种植桃花的现象并不多,即使是在极有利于种植桃花的地方。这也是一件颇可遗憾的事情。就是在桃花喜欢生长的地方,人们并没有将桃花种植面积最大化,更没有将桃花产业开拓最大化。一株桃花种植其实不足道也,几株桃树也不足道也,然而,通过量变达到质变,最终必然会形成桃花景观。这种大面积种植的景观与小规模种植的桃花相比,其效果只能用天壤予以区别。
桃树,作为佛堂古镇过去的景观主角,也作为河流边最宜种植的一种景观植物或者经济植物,在佛堂古镇应该早日种植回去,非但如此,而且还应该大面积地种植。这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明代人卓人月在他的《桃叶渡种桃赋》中曾经这样感慨:
秦淮无桃花,犹岁时无春,女子无眉色,文人无文心也。
正如其它诸多自然之物的美一样,桃花的美丽是人所共知共赏。在此外,卓人月把桃花在溪流河流边的点缀作用,提高了非同寻常的地步。
中国的世外桃源,在一片桃花中,中国的美学极致,也在一片桃花中。让我们从桃花开始追寻桃花吧,也许我们便能找到世外桃源。
故乡的桃林固然漂亮,但如今已经是坦荡无存。由于各种不便启齿的缘故,历史上的桃花林被砍伐殆尽。其在佛堂古镇的命运戛然而止。清代慈溪人叶士俞《桃花赋》中的一赋句可以作为我的结尾,最恰当其分地表达出了我此刻无可奈何的心情:
对朱鄱之摇曳,嗟无力以护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