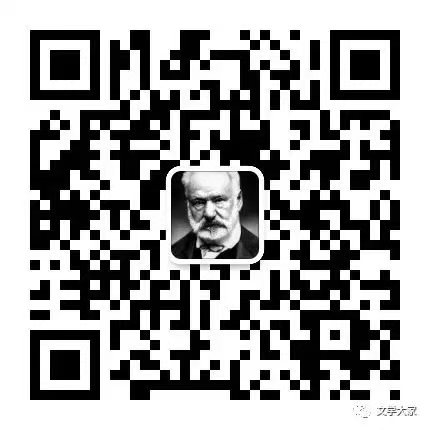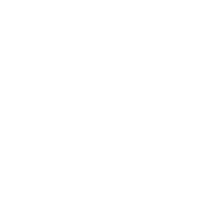
文学大家
media group
放眼未来,着步全球
多方位文化传媒策划
来呀,可爱的小朋友们,让我们建造一座中国园林
来呀,可爱的小朋友们,让我们建造一座中国园林
用我们稚嫩的小手,在我们的古镇建造一道美丽的风景
我们爱故乡的甍宇、飞檐,我们爱这里的阑干、挂落、窗棂
老宅和古屋星罗棋布,随处有巧笑倩兮、丽影盈盈
这是一座精美的中国园林,就建造在上塘沿我家小小的客厅
它悄然坐落在那沉稳的水缸中,那里有仙壶般的玄妙秘境
我们造不起拙政园、狮子林,更造不起长春、绮春和圆明
但是,我们可以造梦啊,我们把美梦做成世外桃源般的盆景
古镇的地下水成为小池的源泉,景象胜过了西湖风月无边
白天,排门外的阳光进来悄悄爱抚,水池里顿时波光潋滟
黑夜,白炽灯照耀此处,又如同沧浪亭的周遭梦幻如烟
中国园林里的池水啊,真希望像晋祠的难老泉长流千年
搬来灯泡厂里堆堆废弃的炉渣,清洗后块块风格棱嶒
叠垒起一座座突兀簇拥的假山,高耸入云直穿碧空
那座座假山峻岭起伏,瘦骨嶙峋的样子宛若自然天成
就像亿万年前的岩浆,喷发成今天的湖光山色和贝阙珠宫
为挖到陈年百古的苔藓,小伙伴们又来到了吴棋记的老院
把苔藓覆盖到所有的假山上,将山阳和山阴都用苍翠点染
再到上塘沿掘来几株树苗,错落有致地点缀在山巅、山腰
啊,多像那郁郁葱葱的云黄仙山,满眼滴绿啊一片妖娆
然后到义乌江畔的湿地里,到浩瀚无边的金色细沙里
精挑细选那颗颗石砾,各色各样、光滑如玉而又纹理细腻
让这些玛瑙装饰水底,让金鱼们在梦幻般的池底畅游嬉戏
多么像富春江的七里泷啊,湍流下的游鱼细石清澈见底
哦,应该还有数株水草,让它们自由地在柔波里随意招摇
于是来到下塘沿的茭白丛边,捞来了一缕缕一丝丝的翠绿
在水中央沉浸,好比那天女的裙带一样在空中东飞西飘
啊,生机勃勃的中国园林啊,天赐的色彩美得无可比拟
我扶腮沉思,该怎样营造“远上寒山石径斜”的绝佳诗意?
母亲拿来些水泥,于是我自个儿倒水、搅拌,小心翼翼
铺在林间和山脊上,曲曲折折的台阶如同泰山上的天梯
用石块架一座天桥,横亘在深不可测的山谷和悬崖峭壁
最难建造的是中国塔和中国亭了,飞檐与华盖最为适宜
那用什么代替?就用父亲送给我的那个宝塔瓷器玩具
再到樟树脚边的木器店里,捡几块木块和几根细细的木枝
啊,高高的亭子像雄鹰矗立在山顶,“直上千尺看云低”
最后用哥哥给的课本纸折一艘小小的船只,飘浮在那波涛
在船舱的侧面开几扇窗,用红筋泥塑一位诗人冥思苦想
把细细的棒冰棍插进梢公的掌中,像极了撑在水里的长篙
啊,那位忧愁的孤客,是否感伤“夜半钟声”到了“客船”
万里山河就在尺寸之间,亭台楼阁就是中国人快乐的天堂
谁阻挡我们看外面的世界,我们就自己建造自由的天地一方
梦里常见的中国园林啊,早已经烟消云散,而古镇亦已老去
人工的雕饰和自然的曼妙啊,在回忆中与地长存,与天同齐
题解:大概是五、六岁时吧,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古镇佛堂老家生活。我儿时的玩伴、对面邻居王海松伯伯之子王国斌于家中一水缸中自做小小中国园林盆景,不胜艳羡。当时只要周围的小孩有新的玩意,便立刻跟样学习,如他人摘桑叶养蚕宝宝,我便也开始摘桑叶养蚕宝宝;他人玩火柴枪了,我便也想方设法制作一把火柴枪与小朋友们一起玩起打仗的游戏;如他人做轴承四轮车了,我立刻也想要有归属于自己的一辆,如不能得之,则便魂牵梦萦,在梦中也要尽快骑着它在晒场上奔驰,那种望之不得、丢魂失魄的样子是极其可怜的。总之,就像当今的小孩,看到谁手中有奥特曼卡片玩具,自己便无论如何手中也要拿上几张炫耀炫耀一番。如此跟样学样的做法,不仅使自己得了许多新颖的不落后于时代的稀奇快乐,也使自己与小朋友们极为融洽地玩在了一起,成为一个有小伙伴的人,一个有朋友圈的人,而不是一个寂寞孤独的“孤家寡人”。既然王国斌建起了江南园林,因此,我也便效仿着在家中搞了一个小小的水缸,自个儿捣鼓起小小的江南园林。我深刻地记得,当时我亲手把江南园林盆景建好以后,王国斌进到我家来看我的作品,他明显地露出了诧异惊奇的表情,不过,在那表情中也隐藏有一丝丝的窃笑,大概是窃笑我怎么也能制作出如此惟妙惟肖的江南园林盆景吧——儿时的小伙伴们虽然年纪小,但是相互之间还有攀比心理,不像现在的儿童们攀比谁谁衣服好和谁谁有钱、谁家家长做得官大(这是不是说明世风日下、人心不纯、拜金主义和官本位主义盛行了呢?)而是攀比哪个的玩具更新颖,更有趣,更有特色,更精致,更像模样,所以,当我的江南园林盆景与王国斌的江南园林盆景不相上下时,他的些微揶揄也在情理之中。纵使我做得不比他的好,但他恐怕也是要来挑一挑刺的,以免得对手骄傲,以至于在小朋友们中占据更高的地位与分量。
上塘沿我家小小的客厅:我在佛堂古镇的老家是一座中国式阁楼,地处千年古镇佛堂竹园村上塘沿,自祖父辈开始居住在这里。所以这是祖屋。阁楼分为二层,全为木头结构。门为排门,材料天然,别有韵味,颇具中国特色,后来不知何故,排门一律撤销,改用极不好看、普通至极的水泥墙。奇怪的是,在排门应用期间,虽然并没有安徽一带惯有的以青砖墙作为外面防火之用,但印象中似乎也从来没有着过火,不仅老屋未着火,隔壁邻居家同样材料、同样结构的老屋也未着过火。倒是改用了水泥砌筑的墙壁以后,我家对面的一排邻居房屋着了一次火,将许多房屋烧成残垣断壁、面目全非,最后推倒重建,盖起了现代水泥楼,再也没有了之前所谓的中国阁楼样式。在我家的阁楼,一层外面是客厅,里面是厨房;从灶台后登梯上二楼,就是寝室。坐临窗的美人靠上,可俯瞰我家门前悠长的鹅卵石巷。 按现在义乌人时新的话讲,我家老屋属于“有天有地”的人家,如果在城里,则是可以出租当房东的,一楼可以出租当仓库,二楼房东自住,或虽然并没有人家的“四层半”(义乌农村拆迁重建特色,多用“四层半”形式,建成后一至三层出租给房客,四楼自住,四层以上的半层种种菜,自给自足)多,但我们也有二层,至少当一个食租阶层,是极为惬意逍遥的。
灯泡厂:义乌佛堂灯泡厂,此厂距我家老屋仅数百米。厂子门口之面貌回忆起来依然分明,至今时不时在脑海中浮现。小时的我往往在路上朝灯泡厂门口里面一瞅,则可见破碎灯泡在道路一侧堆积如山,颇为凌乱。大概做灯泡要烧许多煤的,煤渣废弃不用,因此我们小伙伴们便可随意拿来做假山。
七里泷:年幼时,每年要从义乌县城汽车总站乘坐长途公共汽车,与父亲、母亲、姐姐一起到临安于潜外婆家过年,当时到于潜的道路选择性不多,必须从极其险峻的马岭走,马峻上的路多在峭壁上,坐在车上,就如同人在天上,或者人在云间,窗外看到的就是万丈深渊。过此路虽然危险,但也是“有险无惊”,因司机常开这条路,而我们也是司空见惯,所以见怪不怪,处险不惊,若无其事的。过此路的一大好处是必经过名闻遐迩的富春江七里泷,记得我自己经常趴在汽车的窗户上看七里泷的水奔腾喷涌,狂涛恣肆,滔滔不绝,尤其感觉那水是世间最为清澈的溪水,上面白白的浪花像雪,像玉,下面青青的颜色极浓,就像翡翠,印象极为深刻。只可惜,当时,年幼的我对这种美也并不太懂得欣赏,大概还是想外婆家里的人间美味——猪头肉倒要多一些吧,或者还有大舅舅家的糖醋排骨——这都是小时候印象中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但是,经过这里的好处到来后来便极清晰明显了。由于我多次经过此地,便如提早经过了实地考察一般,于是,当初中时读到吴均的《与朱元思书》时,便感同身受,较绝大多数没有机会去过富春江七里泷的同学们,肯定更能理解吴均美文之妙及富春江水之美了。此文我是极为欢喜的。我想,世间再也没有谁能写出更好的描绘富春江的美文了,在这里,特地将这如天籁一般的骈文抄录一番,以助理解:“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我想,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特色山川之美的感受与理解,以至喜爱,大概就在这些时候埋下种子的吧。至少我是这样子。这类文章还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萌生了我对中国尺牍文学的偏爱。因为,《与朱元思书》是一封信,信能写成这样,好比字里行间镶金嵌主一般,又好比春天美景之姹紫嫣红,美不胜收,佳丽清新,历历在目,犹如千里江山图一般的中国画,还真是让人有惊艳之感。除非这个人对中国文字没有感觉。所以在中国,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种类,即中国尺牍文学。后来我养成了对中国尺牍文学的爱好,乃至经常搜集中国尺牍文学书籍,应该与对《与朱元思书》的阅读乃至能够背诵大有关系。我负笈成都时,在成都古籍书屋十分留意此类书籍,搜罗了几本,至今犹存,亦是一件乐事。后来还在孔夫子网上专门搜集相关书籍,成为一种雅好吧。
下塘沿:我家居住的地方叫佛堂镇竹园村,该村最大的地理特征有两个,一个就是地处义乌江边,长江紧贴着竹园村而过;另一个就是村子南北有两个塘,至今仍存,通过高德地图是清晰可见的,也十分明显,两塘者,北为上塘,周围地理方位于是称为上墉沿,我家就住在上塘沿;南为下塘,周围地理方位于是称为下塘沿,我叔叔家就住在上塘沿。两塘印象均十分深刻。此下塘沿,印象中昔日水滨多植茭白,恰似古人佩带的碧玉腰带一般,包围着池塘,也包围着临水的村庄,平时丛叶青青,如刺如林,笔直冲天,十分茂盛,像极了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岸芷汀兰,郁郁菁菁。”初中读此记时,并没有看到过“岸芷汀兰”,亦不懂得此番究竟是何种景象,但是,既然是“岸”、“汀”啦,想想与故乡下塘沿水边的景象是差不多的,于是,便极其自然地也是想当然地把“岸芷汀兰”与家乡下塘沿的茭白丛林联系在一起了。盖此亦是故乡风景优美的一大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好处。读及曹操《观沧海》中之佳句:“水草丰茂,洪波涌起”,亦令我想起下塘沿的这一片茭白丛林,用“水草丰茂”来形容实是毫不为过。至于“洪波涌起”,当然没有这样的气势,但是在历史上,我猜测,佛堂下塘沿的规模绝对不止于此。中国人习惯于往水边丢废弃物件,抛洒杂物泥土,通过日积月累,脚下的土地慢慢向水中蔓延,于自然而然中完成了“填塘”的工程亦完全有可能。上海崇明岛这样的大岛,其脚下的泥土都是由长江水带来的泥沙千万年沉积下来而形成的。在八十年代,我偶然一次经过下塘,曾经看到过竹园村村民在下塘里大规模捕鱼捞鱼的现象,可谓船舶翻滚,万鱼腾跃,众人欢呼,波澜壮阔,浪花飞溅,如同海洋上“开渔节”时渔船捕鱼般的壮观。可以想见,如此既有茭白收割之利,又有鱼类捕捞之乐的地方,在缺乏粮食的古代是得到极大的保护与开发的。如今,经过数年的“五水共治”,下塘的水得到较大的改观,但与当年不能同日而语,如果学习一下中国园林学和生态景观学,当会懂得利用植物本身与水中鱼类动物本身的美化、净化,将可以得到更好更持久的可持续的生态保持效果,且可以兼收发展美丽乡村、振兴旅游产业之功效。下塘小则小矣,然而不可不精致,如果稍加策划整理,恢复茭白丛林,投之以鱼,或将形成茭白产业、捕捞体验产业也未可知。
樟树脚边的木器店:佛堂新市基上有一株老樟树,约有八百年历史,直径1.8米,往往成为人们在新市基拍照留影时的背景,属于地标植物。从樟树脚往北面的老街上走,会有一家木器店,别看这是一家普普通通的木器店,跟我小时候的快乐也密不可分。为何?因为小时候我们经常玩的陀螺啊、木头手枪啊、四轮平板车啊,制作都得到这家木器店不可。我清楚地记得,父亲远在四川,我自己也做不来陀螺,看到同村的小朋友们抽陀螺玩得不亦乐乎,十分羡慕,但也一直没有向妈妈讨要,苦闷极了,等到爸爸从四川探亲回到老家,我才叫爸爸到这家木器店替我打了一个陀螺。诶,几分钟的功夫,就实现了我多少个睡梦中都记挂的梦想,这真是一种难以忘却的记忆啊。那个四轮木板车,简直太讨我的欢喜了,也是经过好长一段的波折,我才搞到手。这车应该是妈妈找人在木器店帮我做的。所谓的四轮木板车,就是下面四个轴承当轮子,上面架着一块木板当坐垫,还有一个把手供我双手掌握,可以转向,相当灵活,制作简单,就像李书福说的那样:“汽车就是四个沙发加一个发动机。”当小朋友推着坐在四轮平板车的我在晒场上奔驰时,晒场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唬唬唬”的响声,那种儿童特有的喜悦,是当今的成年人快乐不太好替代的,也无法理解的。我想,童年的快乐可能不在于玩玩具本身,而在于能够与小朋友们一起玩,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地闹啊,打啊,乐啊,笑啊,这大概是人间至乐吧。